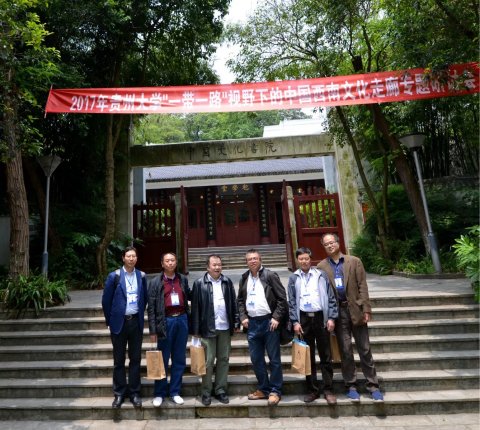
贵州大学的老师来了电话,说是要我参加“古苗疆走廊”研讨会,还说,这是在“一带一路”视眼下的。说实话,我真的有那么一点不适之举,因为,谁都知道,“一带一路”重点圈定了18个省,贵州没进入菜单之上。而邻的重庆、云南、广西、西藏罕然在“目”,作为一个“三不沾”的省份当然最感“悲催”。贵州目前的发展势头良好,优势产业明显,自身定位清晰,长江经济带规划占一席之地,高铁网也逐渐完善,去年经济增长率名列前茅。居然没有写入菜单,而我们贵州舆论板块并未掀起波澜,这不得不说是被遗忘的角落了。后来,我在一个研究生的说服之下,打算又去被“忽悠”一次罢了。
宋永泉老师是有备而去的,他邮去了文稿,而我则不然。下塌的酒店叫丽枫,档次自然很高,报到的人居然全是名校、研究学院等大排级的专家、教授、博士和研究生,共二百五十多号人。而我们是全会唯一来自基层的“土专家”。我想,只要我们不发言,谁也认不出我们是“土”货。话是这么说,认识我们的人却不少,领国家津贴的云大教授陈庆德、客居大陆的台湾学者马腾岳等则认识我们来。好!猪鼻子插根葱——装象吧!
“古苗疆走廊”是个文化概念,类似于“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是贵州大学几个年轻的学者杨志强、曹端波等提出来的。其目的也就是让贵州发声,也就是在贵州语境下的“一带一路”,强化“文化走廊”概念,注重文化在通道的价值及其地理空间中,各种文化形态的互动、交融与互生,并积极探索文化走廊和民族地域一核对多元文化价值和现代意义。
早在2012年,贵州大学的老师就莅临偏桥小镇。那时,我对这一概念是模糊的,通过再教育,我仿佛也能“一知半解”了。这几年来,我参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要说“研究”,其实是在做一些基础性的调查工作。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几年来,我自备着干粮,走访了明季以来所谓的屯、寨、堡、驿道、水路等。其中村落就走了一百多个村寨,写了一百余万字的小东西。我的想法是:战略层面不是我考虑的,我想要做的是驿道两旁还能留存什么东西,以便官方决策时的参考。
偏桥明代卫城,处在“滇前楚尾”,我曾经说个,在苗疆还是化外之地时,偏桥是中原王朝进入大西南的跳板。“偏桥”,早在唐代就出现过,它是古牂牁的属地。那时的偏桥为“蛮地”,因为是“蛮地”所以才“无徭役”。《旧唐书》上说:“牂牁蛮,首领亦姓谢氏。其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其首领谢龙羽,大业末据其地,胜兵数万人。”我们知道,偏桥在唐时绝对还是“化外之地”。没有纳入中央的统治范围。《明史》讲得清清楚楚:“贵州为内地,当自镇远始矣。”也就是说,偏桥东面四十公里的镇远才是中央王朝的地盘。宋时安氏就设“偏桥硐蛮长官司”,自安祟诚始,至安德千败落结束,前后历15任正官司,时间长达440年之久。是不是受制于宋,没有说明,可能是“羁縻制度”而已。
从战略层面来说,偏桥的“地位”很高,贵州巡抚彭而述在他写的《碑记》中说:“沅居楚西隅,隶楚。偏桥居黔南孔道,属黔而兼隶楚,往有偏大沅抚军之设,取名于此。以为滇、蜀、黔、楚要枢,故抚军驻节两地,从中持缓急。”清代著名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叙》中,对偏桥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如下评价:“偏桥,在镇远府西五十里。自湖广沅州而西,四百四十里而至偏桥。自贵阳府而东,三百六十里而至偏桥。盖辰沅之指臂,贵阳之噤喉。偏桥警而东西隔绝,粮援中断矣。国家幅员滇洱,置驿四川,不如取途湖广为径。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重贵阳不得不急偏桥,必至之势也。……二十五年,置卫,地在贵州,而军属湖广……嗣后苗蛮有警,必急扼偏桥,而不轨之徒亦复眈眈于此。杨应龙跋扈于前,袭偏桥而楚黔中梗;安邦彦跳梁于后,犯偏桥而黔贵几危。所以国家于湖南建节而以偏沅为称者,盖偏桥在三省之交,苗蛮环错,四顾皆险,其在贵阳,尤为上游之形胜也。”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杨应龙叛乱。攻占偏桥48屯(在现在的湄潭县境内),并攻陷偏桥卫城,使朝野为之震动。在征剿杨应龙的过程中,湖广有的官员把对贵州的支援看成是“舍已为人”的分外之事。因此,湖广不仅不派兵援救,连军饷也屡催不至。在这种情况下,云贵总督李化龙愤然上疏万历皇帝,痛批湖广官员的短视行为:“……夫偏桥走全省之道,偏桥不守,则祸中于楚。今戮力会剿为黔即楚也,非舍已耘人之比。”也就是说,如果偏桥失守,不仅贵州、云南不保,湖广也会深受其害。天启三年(1623年)十一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在上疏中就说:“天下有时急,而人不得独缓;地重而人不得独轻者。最急莫如辽左,而蓟门其咽喉也;其次莫如滇黔,而偏沅其门户也。”可见偏桥在明朝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花阶路是当地人对古驿道的称呼,这种路也有人叫它马路。就施秉而言,花阶路是苗汉的分界线。明代郭子章曾写书曰:木叶冲之南为苗界也!现在对于这界我们似乎关心不大,其实,在明代,明朝为守这条古驿派来了大量的军队打通此路,将苗族驱赶于驿道之南,然后驻扎坚守,目的是阻止苗人犯驿道,阻塞通道。就是在“木叶冲”之地,设立苗汉界碑。至张广泗犯清江,设新疆六厅,几千年前的苗疆从此进入中央王朝的视线。
现在我们从来提起苗疆并非从提前世民族间的恩恩怨怨,而是要将还在活跃着的古驿各族文化加以诠释,让文化融入鲜活的时代脉搏,为其打造成成光照全球的文化亮点。在偏桥一地,直到今天,依然积淀着深厚活态化的文化。中国的“龙”文化玩得最转的地方不是北方或江南,而是偏居一隅的施秉,水龙、亮龙、独木龙、草把龙、祈福龙等等,被这小小的地方玩到了极致。中国汉字的活化石或许不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而是产于这里木棒上的“刻道”歌棒。丝绸之路的丝绸不是江南汉人所做,“发明权”当是这些曾居在江南的蛮苗,中国文字望文生义,其实“蛮”,繁体字写作“蠻”,两边一个绕丝,中间一个言字,下面是个“虫”字。解读下来就是:穿着华丽丝绸服装,说着一种汉人听不懂的鸟语,居住在有鱼虾虫子游荡河流岸边上的民族。这就是蛮苗或蛮族。
这里的苗族能将自己的远古居住地用古歌的形式留言存了下来,苗族《大歌》把人类从猴子变成人,再从群婚家庭至对偶家庭说得明明白白。《开亲歌》讲述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故事。苗族古代有文字吗?苗族人也说得清楚,一部《喀都浏席》让你读懂她曾经有文字文明的历史。……由此,我们说这是一个文化之地,骄傲和自豪之地。
参加论坛之后,我得到很多的启示,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文明进程中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别要把知道“OK”这样的文字,就以为占领了文化的高地,就掌握了文明的“制空权”。历史是一个过程,我们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冲昏头脑之后,还望历史,我们依恋着真正的文明,乡音乡愁给了我们精神的依托,是给我们醒来时的良药。不要把“一带一路”不把贵州列入国家战略层面而感“悲催”。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贵州一定会“后来居上”。贵州省已将“推动苗疆文化走廊建设”纳入自己的菜单。民族文化旅游是亮点,所谓落后的民族文化此时正正“蝶变”,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
“西南文化走廊”的人们也要发出声音。正如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所说的:我们可以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世界各民族的世界性民族走廊概念。“一带一路”隐含着互惠的概念,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发展,现今我们有必要将过去那种互惠观念的文化无意识转变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即一种建立在个体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很重要,我们要在全球视眼之下去诠释。
阅读感言